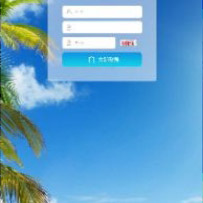于其超
我对童年家的印象,逐渐像轻烟一样飘失了。在家的概念中,地域、环境、屋宇应该是次要的,主要是亲情构成的温馨的气氛。可是这正是我童年的匮乏。父亲早年离家未归,我对他的印象比轻烟还淡薄和渺茫。家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像祥林嫂一样孤独的女人。从小我就与这个女人相依为命,我的娘始终伴随着我,呵护着我,惦念着我。长大了,我参加了革命,有了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家。这个家中依然有我的高堂老母,其实我的老母何时住过高堂?在老家时我与母亲蜗居的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低矮的小东屋,夏天像蒸笼一样热,冬天则是座典型的寒窑。外边的家,我们依然没有高房大屋,都是赁住人家的厢房或倒座(不见阳光的南屋),依然简陋,依然窄狭,依然终年缺少亮度、冬天缺少温度。因为我有了妻子儿女,上有老下有小,具有了真正的家的温馨,这个家不管条件多差,我总算知足地有了一个满意的平静的港湾。
以后命运把我送去了劳改林场,我远离了这个家,而且一别二十余载。家就成了一个日思夜想的惦念。我是多么想回去看看我的老娘,我的女儿、儿子和我那又羸瘦、又懦弱、又善良的妻子。我的妻子,原先那紧绷着的极富弹性的胸脯,因哺育了几个儿女,自身又缺乏营养,如今也瘪了下来,乳房像两片空口袋似的松垮垮地贴在胸上。看了我就心酸,我觉得对这个从深山里走出来、铁了心依赖于我的妻子有太多的愧疚。就是这个女子的弱肩,为我担起了扶老育幼的家的重担。
我被集中到一个林场劳动改造,其实离家只有四十里,这四十里却像远隔千山万水,真像隔着一道监狱的上着铁丝网的高墙。失去自由的距离是没法以里程计算的。
终于有一个夏季,大雨连绵,几天不能下地干活。场方便很惋惜地组织这帮姓“右”的廉价劳动力开会学文件。我惴惴地蹭到办公室,向主任提出了请一天假的请求。因为前两天家中来信,告知我妻子分娩了,据说场里为了对我们负责,来往信件都要检查,因此场里知道这件事。主任宏恩浩荡,允许了我于晚饭后可以回家看看。如果天气开晴,明日上午就得赶回来,如果老下雨,我可以明天晚上再回。
我感动得几乎流了泪。坚持学习到晚饭钟敲过,匆匆找出平时节约下的饭票,到伙房买了八个棒子面“火轮”(大师傅为了省事,两手一合作成的火轮状的、没有窟窿眼的窝头),用一件破衣服裹严实,抱在怀里,饿着肚子冒雨上了路。我必须争取时间紧走,为的是能在家与亲人多待一会儿。
路很难走,胶泥地又滑又黏,一会儿两只布鞋就粘得榔头一样拔不动脚了。我索性脱了,光脚丫走,把两只沉重的泥鞋提在手里。胶泥仍然粘脚,我趔趔趄趄,想提高速度很难,心里着急,一会儿便外面淋雨、身上出汗,小褂全溻透了。
雨仍然不紧不慢地下着,夜幕逐渐浓重地笼罩下来,但我仍能大略辨清道路。为了少粘泥,我就单走在路边长着草的边沿处,草上面有水没泥,踏在上面沙沙有声,形成了鼓舞我加速前进的愉快的韵律。可是不时感到有蒺藜狗子扎我,我没心思理会它们,它扎它的我走我的,最多在草上搓一下脚板,忍着疼飞速前进。
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临近城里时走迷了路,踩到人家一片倭瓜地之中,大倭瓜把我绊了好几跤,从软泥里费劲地拔着双腿,雨水汗水迷糊了视线,挣扎很久才重新走上大道。
要在平常,四十里地,我三个小时准能拿下来,这次我却崴泥了近六个小时。天还没黑就起了程,到家时已将过午夜。
进到院里,我先伏脸到窗纸上,窗户里面就是一盘土炕,这是我们一家老少三辈的暖窝。静听了一阵里面老小的匀称的呼吸声和轻微的鼾声。我又高兴又激动,终于到家了,就要看到亲人了,我再不能作半分钟拖延。
“娘!”我确实是轻轻地叫的,娘却马上听到了。只这一个字,她就辨出了是她儿子。
“青青!快起来去开门,是你爸爸回来了!”娘在屋里说。
“爸爸!爸爸!”大女儿青青,拉着了灯。光脚板踩得当地呱呱响,给我开了屋门。
“哎呀青青,你怎么光溜溜的?”我看到女儿一丝不挂,迅速钻进奶奶的被窝。
“是爸爸,我怕什么?”孩子在奶奶的被窝里欢喜着说。
妻子醒了,含情脉脉地望着我。
“下着雨,道该多难走啊!”她说。
我走过去,伏身亲了亲她身边熟睡着的新生小女儿。很香甜,小脸上奶味很浓。
儿子刚刚 (儿子的乳名)也醒了,揉着惺忪迷离的睡眼说:“爸爸,你怎么老不回来?”
“刚刚!爸爸这不是回来了吗?”望着多时不见的儿子,我有些心酸,努力装出欢乐的声调说。
“爸爸!我要挨着你睡。”儿子说着伸手扯住了我的湿漉漉的衣襟。
“刚刚想爸爸了吧,爸爸当然要挨着刚刚睡。你等我把脚洗干净了呀!”
我草草把腿脚擦洗干净,赶紧贴着儿子躺下,我楼住儿子瘦弱的小身子,眼眶里盈满了泪水。这个孩子渴望得到父爱,可是他像我小时侯一样,想见见父亲竟也是如此艰难。
我身后就是那个新生婴儿,婴儿那边,妻子伸过手来,摸摸我光裸的脊背:“瘦了,吃的饱吗?”妻子问。
“吃的饱吃的饱!”我抑制住泪水喑咽地回答。
“走到这咋晚,准饿了,篮子里还有两块饽饽,去吃了再睡。”娘也对我说。
“吃了饭来的,真不饿。”我舍不得松开搂着儿子的手臂,我想我肚子里的咕噜声娘是听不见的。脚底下蒺藜刺儿的扎疼我也能忍住。
儿子头枕在我的肘弯里很快又睡着了,青青也睡着了。一盘土炕上,三个熟睡着的小生命,三个睁着眼思忖着难以摆脱忧患的大人,组成了这个家的极不和谐的沉重的气氛。这就是我当时享受到的幸福。这就是我的家。
谁知第二天天公不为我作美,风起了,云散了,天晴了。也就是说我必须于上午回场了。
早饭我没有吃,把几个金黄的窝头热在锅里,看着孩子惊喜的面容,泪珠又在眼眶里打转,饭后吻了吻孩子们,到躺在炕上的妻子身边站了一会,和我娘说了一声:“我该走了。”就毅然上路了。
天晴了,道路虽泥泞但很明亮,我终于于午饭前赶到了林场。谁知,雨刚停,田间积水片片,下午仍下不了地,老“右”们依然只好学习,找几个不老实改造的典型开批判会。我听着那些懒洋洋、装腔作势的发言,心却仍在家里,儿女欢笑、老娘愁闷、妻子凝重地沉默,一直盘桓于我的心头。
……
月光如水,灌满了我的宽大的居室。宽绰舒适的大铺上,只有我一个人躺着。此刻我唯一的意识是,我是在哪里?怎么只我一个人?我的家怎么这么明亮,这么宁静?
稍一凝神静思,这才发现,适才是作了一个梦。梦中清晰的情景正是我四十年前从劳改林场回家时的经过。竟然如此真切,如此琐细,如此与实情分毫不差。忽略的只是我在回场的路上饿极了,拐进一片棒子地里,啃吃了人家一个生棒子的情节。
噢!我现在是在家里,不是在劳改,不会有批斗,无须惊恐。我为什么心跳得这么厉害?为什么泪水浸湿了枕头?噢!我那些亲人都不在我身边了。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如今我已经老了。女儿们都出嫁了,成了别人家的人啦,儿子小刚早夭折了,不是在十岁时死于车祸了吗!我又记起了薄皮棺材里那张惨黄的小脸;我那老娘在三年前就作古了。就着月光,我再摸摸身边,怎么我那老伴呢?不对啊!那个少言寡语的老伴,始终是与我相依为命的啊?晚年生活好了,她已经发胖了,她到哪里去呢?我下意识地又摸摸我身边宽大的床铺。
月亮西斜,晚秋清冷的月光直照我的床头。这清冷的光,终于使我神志完全清醒了。啊!妻子也死了,是在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突然地发病,与我不辞而别的。
什么是家?难道家就是这所房子吗?不!家是亲人,家是亲情,家就是妻子儿女。如今我徒有宽房大院,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的家了。只我一个孤老头子怎能构成家的概念?这个干净的院落,这所宽大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喧哗,没有了争执,没有了欢笑,也没有了语言,因而没有了温情,没有了家的意义。白天和夜晚都死一般的寂静,像座坟墓般可怕的寂静。一切的一切都像烟雾一样飘散了,像我远远飘逝了的那懵懂的童年。惟有我孤自对亲人的思念,永远像座沉重的磐石压在我心上,要压断我的脊骨,要榨干我的泪水。
我还是得感激神灵,总算给了我这个温暖的梦,让我一家人再次相见,给了我们一次虚幻的团聚。
泪水突然汹涌而来,在这空阔的房间里,谁也听不到我的呜咽。于是我难以自制地喊出声来:
“我的家在哪里?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寂寥的夜,空阔的房间,周围世界沉浸在甜美的梦中,没有人听到我的喊声。
我终于悟出:人生原本就是一场梦啊!这场梦还没有全醒,只能继续作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