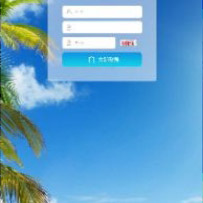夏日,麦子收下来了,庄稼主可以吃几顿白面了。
妈妈和婶婶在灶房烙饼,我们山东特有的那种大张的单饼。已经烙了一大摞,我饿了,从中间抻一张软和的,对折起来,拿到酱缸前,用木铲抹上一些酱,再把案板上洗好的韭菜拦腰一刀,不要叶儿,把大梗子取一绺,铺到饼上,卷起来,康康地大口嚼,那个香啊。
这样吃上两张,我就打饱嗝了。蹦蹦跳跳地找我的狐朋狗友玩去了。逮知了或下河。任爷爷怎么喊我吃饭,我也权当没听见,常常是傍晚才回家。
爷爷问我:玩水去了?
我慨然回答:没有,绝对没有。
过来我看看,爷爷说。
爷爷在我的腿上用指甲划了几道印儿。然后骂道:王八羔子,说瞎话。
爷爷狠狠地指着我腿上明显的白印说:骗得了我?刚下过雨,河里正涨水,你不要命啦?
于是我背脊上狠狠地挨了一掌。
说!记住了吗?爷爷厉声问。
记住了!我回答。
爷爷的那句命令,就像我肚子里那两张单饼一样,很快就消化了。
第二天照样和我的朋友一道,下河玩水。
河不远,就在我们村东约半里地。整个夏季我们几乎天天在这里消磨时间,我那些狐朋狗友都是我们一个村的,论家族或乡亲辈,有的我应该叫叔或爷,当然也有人该叫我叔,但我们不论这些,一律叫小名,柱子、铁蛋、狗剩之类,喊的高声,答应得也响亮。
我们玩水花样繁多。狗刨打扑腾那不算花样。潜泳、仰泳、踩水才有技术性。我们极富冒险精神,都喜欢深水,雨后涨水时,水深溜儿急,我们下河的兴致最高,简直要玩疯了。常比赛顶着水溜儿,看谁游得最远,坚持时间最久。看谁能从深深的河底下抓一把泥上来。踩水较难,要立在深水中,把肩膀甚至胸膛露出水面,要两手两脚一起用力,很难也很累人。
消闲的玩耍也有。那时农村都穿带裤腰的长裤,我们把长裤在水里泡湿,粗布湿了就不透气了,把两只裤脚用绳扎住,然后提着裤腰在岸上抡,让裤筒里灌满空气后迅速把裤腰扎紧。这样就形成了救生圈样的东西。拿进水里,把身子伏进两个裤腿间,就可以自由地在水上浮游了。那裤子会很长时间不撒气,我们这样等于休息一会儿。
我们也捉鱼摸蟹,往往很少收获。玩水玩累了,我们常沿着河边在水里浮着身子掏岸边的螃蟹洞,这就要技巧了。铁蛋那家伙就很在行,他懂得什么样的洞口里面有螃蟹,什么样的是癞蛤蟆的家。我却常常掏出癞蛤蟆,只好生气地把它扔到岸上。
有一次我和铁蛋专门去捉蟹。我们都脱得光溜溜的,但腰上系了一根裤腰带,把小褂弄成口袋状,掖在裤腰带上,准备装螃蟹。从早饭后到日头偏西,两手泡得又白又涨,我只抓了三只,而铁蛋却弄了十多只。他看我的太少,就慷慨地扔给我四五只。
螃蟹很小,最大的也就茶碗口大,但拿回家十来只螃蟹,我爷爷奶奶看到还是乐了。奶奶在小锅里放点水放点盐,把螃蟹卤得焦黄,人人都尝了尝。
“以后不许去掏螃蟹窝了,掏出长虫来就麻烦了!”爷爷很严肃地警告我。
我自幼胆小,尤怕长虫(蛇),以后真没再掏螃蟹。但我常见铁蛋掏,也并没见他掏出过长虫。
我童年的欢乐在夏天,而夏天的欢乐主要在于村东那条河和我村里那些童年朋友。如今老了,那些童年朋友多数不在人世了。我的铁哥们铁蛋(实际他是我的乡亲叔叔),比我大两岁,参军比我早,那一年他牺牲于解放洛阳的战斗中。
唉!真想他们啊!只能到那个世界能再聚在一起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