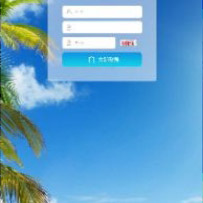■ 董凤琴
离开故乡48年了,总是想起小时候生活过的小院。春天的小院是被柳树淡绿色的枝条儿抚摸醒的,柳芽儿鹅黄了,淡粉色的桃花开了,蜜蜂扇动着小翅膀飞来了,桃花太喜欢这些远方来的小精灵,它们的小脚丫儿一踩在桃花上,那红脸的桃子就要来了,大杨树、榆树跟趟儿似长出绿叶,过不了多少天,绿色就漫盖了小院。娘从葫芦瓢里握一把高粱米,嘴里低声呼唤着“咕咕,咕咕”一群母鸡和一只大公鸡象听见召唤,争先恐后跑到娘的身边,娘总是把手里的高粱米撒得匀一些,那只啥食都争着吃的芦花鸡,总是能抢占有利地形。春天,父亲自行车后面总是绑着好几根小树苗儿。
我们是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在供销社当采购员,是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母亲的户口在村里,那时的孩子们户口都随母亲,母亲天天到生产队干活儿,孩子们就在村子里玩耍。采购员这工作走南闯北,一年四季也歇不了几天,可就这样,父亲总会想法春天时抽出点功夫回家忙着种树。
从记事起院子里就有三棵大柳树,我都给它们起了名字,傻大个,是一棵长得最快的树,小细腿儿,同样的天地,它瘦得象个麻秆儿,最喜欢那棵歪脖儿柳,不知咋的,这棵柳树长着长着身子就倾斜了,它好像听懂了孩子们的话,“骑大马坐火车”,一年四季孩子们都愿意骑在它身上说笑打闹,它就象一位脾气极好的老人从不发火。歪脖儿柳枝条儿一绿,孩子们就折几支当鞭子甩着玩,这时,碰见我父亲,他必定大着嗓门儿喊“别祸害树啊”。夏天时,看了一场电影《渡江侦察记》孩子们就折下歪脖儿柳树的枝条围成一个圆圈戴在头上,手握一根木棍儿学着侦察兵的样子,马上就抓“舌头”审审。
父亲带着我们在房后种了两棵大杨树,父母总是说你们要象这棵大杨树一样,健健康康地长大啊,几年的功夫大杨树长高了,它的枝干早就超过了房子,夏秋时节一树的大叶子留下一地儿阴凉,有邻居干活儿累了就到大杨树下乘凉儿,最喜欢在大杨树下听故事,夏天的夜晚,人们吃完饭,搬个板凳,摇一把蒲扇,谈天说地,孩子们躺在地上,有两只小手托着腮帮听大人们讲故事的,有和树叶缝隙里的星星逗着玩儿的。怪三伯是个木匠,年轻时走村串户为村民们打个柜子做个椅子,老了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最怕也最想听他讲鬼啊、神儿、狐狸精变成村妇啊。一阵风吹来大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地响着,大杨树,你也听高兴了吧。6岁的妹妹最喜欢爬大杨树,一眨眼儿的功夫,小人儿不见了,原来她爬到大杨树上去了,她有一个秘密,坐在大杨树岔上看小人书,记得她最喜欢看《雁翎队》,这本小人书讲得是白洋淀人民抗日的故事,当看到戴着大帽子扛着枪的日本鬼子,气得就用小手扣下日本鬼子的脑袋,可翻过一页就是敌后武工队员,她又赶紧用小手找补,大杨树见证了我们快乐的童年。
后来,父亲调到县外贸局当公司经理,这个公司有一项任务就是组织社员们用柳条编各种篮子筐子出口到国外,社员们能得到加工费。我家住村子的最后一排,房后空地较多,父亲就种了柳条,他要看这种柳条能否编篮筐,自己实验好了,就可以让其他人家也种。
院子里枣树和桃树是必须种的。枣树是铁杆庄稼,不怕干旱也不怕涝,只要大水不没顶,枣树依然能奉献给人们红彤彤的枣子,每年秋天打枣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爸爸举着杆子打枣树,孩子们在地上捡枣子,小枣子就好似调皮的猴子,乱蹦的它和我们躲猫猫,盆里装满了,孩子们吃得都打着饱,娘把枣子放在大笸箩里,捡出好枣留着做醉枣过年时吃,留在笸箩里的枣子在阳光下晒干,冬天里这些晒干的枣儿就成了走亲访友礼品了。最喜欢看小蜜蜂飞到桃花上采蜜的样子,它真努力呀,踩过这朵赶紧飞到那朵上去,父亲这时总说“大家都象小蜜蜂一样日子就红火啦”。
每年父亲都带着一家人种树,我家的小院坐落在树林中了,如果您在春夏时节来我家,您会情不自禁地吟诵“绿树村边合”。这片树林差点遭劫,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兴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片小树林就在“资本主义尾巴行列里”一天,大队(现在叫村委会)来了几个人,有的拿个小本子记录,有拿皮尺测量树高,临走撂下一句话,这片小树林的树全部砍掉。
不知父亲怎么和大队交涉的,最后这片种着杨树、榆树的小树林保住了。
又是一个春天,真想回村看看这片小树林,摸摸它粗壮的树干,和我远去的父母说说知心话。